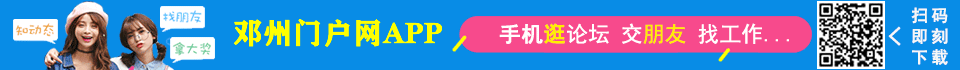四周的空气逐渐变得污浊起来,完全没有了方才的清新舒爽,心旷神怡。
“妈的,这哪里还是游玩纳凉,呼吸新鲜空气?简直就是到这里挤暖包活受罪来了!
靳依林不知是心境不好觉得烦闷,抑或是真的觉着燥热,口中嘟嘟囔囔骂了一句脏话,索性脱下外衣,搭在椅背。
“妈妈,快点!”一个小女孩在草地上蹦蹦跳跳向前跑着,还不时回头催促着,脆脆的童音,宛若铜铃,小女孩有一张圆圆的脸庞,脑后扎着两只黑黝黝的羊角辫,羊角辫上各系一只黄黄的蝴蝶结,仿佛两只真的黄蝴蝶般随着女孩的跳跃,上下不停地翩翩起舞。
“慢着点,人多,别碰着。”一位中年女子紧紧跟在女孩身后,小心的提醒道。
“知道啦呀!”女孩好像觉得自己已不再是小孩子,不愿母亲过于罗唆,有点不情愿的应了声。女孩又向前跑了几步,遽然停下步子,目光落在身边一个个和自己年龄相仿,在父母的牵拉下,欢愉游玩的童男少女们,忽然想起什么,脸上的笑靥顿然消散。待中年女子走近,女孩拉起母亲的手,轻轻摇摆着,充满祁盼的眼神紧紧盯在母亲脸上。“妈,要是我爸爸也在这里该有多好啊!”女孩稚嫩的童音充满了渴盼,又透着一丝丝的无奈。
中年女子怔了一怔,脸色黯然地看了女孩一眼,或许是怕孩子看到她目光中复杂的神色,急忙又将目光移开,茫然地漠视着波光粼粼的湖面,幽幽的说道:“莫提他了。”
或许是女儿的一句话,勾起了中年女子的隐痛,让她说话的语气变得冷漠起来。
靳依林和向东山听到中年女子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,不约而同扭头朝这对母女望去,又同时站起身。
“是李平!”向东山一眼认出面前的中年女子,不由脱口叫出声来,随后推开座椅起身向那母女走去。
靳依林又何尝没有认出眼前的中年女子。不知有多少次,这张面孔出现在他的梦境,扰乱了他的心灵,牵动着他心扉。而如今,仿佛就在倏忽之间,这张面孔真的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,让他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才好。
靳依林的心头一阵颤栗,迟疑了片刻,才迈出步子。
“哎呀,李平,真的是你呀!差一点就不敢相认,你好啊,有多少年没见了?你可富态多了。”向东山表现得很随意,笑呵呵的和李平打着招呼。
叫李平的女子听到有人叫自己,讶然的扭过头,但很快就认出向东山。“是你啊。”李平浅浅一笑,不好意思的说道:“莫取笑了。到这个岁数,那儿能不胖呢。”
“哈哈,就是,就是。噢,这是你的女儿吧,真讨人爱,简直就是一个小李平。”
的确,母女俩都有着相同的脸型,两颊又都透着自然的红润,好似两颗成熟的苹果。
“小玲,叫叔叔。”
“叔叔好!”小铃甜甜的问了声好。
“哈,叫叔叔亲呢还是叫舅舅亲,应该叫舅舅才对吧?”向东山打个酒嗝,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。
“还是那样!”李平跟着笑了一下,问:“你一人啊?”
“呶!还有一位。”向东山眼中闪动着狡黠的目光,抬手朝身后指指。
李平没有看懂向东山的目光,莫名地顺着向东山指的方向看去,正巧对上靳依林投来的那迟疑的目光,不由脸上一热,小声问了句:“你也在啊。”
“哦,在,在。你……一向可好?”靳依林的神情显得有点不自然,两只臂膀木然的低垂着,不知道是否该伸出手去。
“别傻站这儿了,多年不见,十分想念,一块坐坐叙叙旧,走吧。”向东山伸出一只手,绅士般做出邀请的动作。
“不了,不了,明早还要上学,我带小玲去河边坐坐就回了,你们玩儿吧。”李平的目光躲躲闪闪,显得有些慌乱,推辞了一句,急忙拉起女儿就走。
“唉——,听说李平这些年过的很是不好,就一个女人带着个女孩……”向东山看着李平的背影,摇摇头叹息一声,不知是对靳依林说的,还是自言自语。
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靳依林听向东山有意无意这么一说,心中一紧。多少年未见李平,更莫说李平如今的生活状况,唉,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,相逢何必曾相识。
南湖的水在月光的辉映下,变得幽蓝深邃,仿佛那里面藏了许多远古的传说,凝重而又迟缓,似乎不忍遽然就从人们的目光中消失,滞重地缓缓向西南流去,漫过下游的橡胶坝,曲曲折折流淌着奔向远方。 第二章 心绪难言
待靳依林二人坐定,还未聊上几句,夜市摊小老板端上两盘菜,一盘脆炸小白条鱼,一盘凉拌猪顺风。
“您二位还要点什么?就两个菜?”小老板极具经济头脑,一双小眼环顾四周早已坐满客人的小桌,再看看靳依林向东山,目光里流露出一丝小觑的意味,明显是嫌他们点菜少,却占了这么好的位置。
向东山笑眯眯的递过一支烟,小老板哈腰道声“谢了”,接过烟夹在耳跟。
“老板,你看我们俩像是那种小酒量的主吗?”
小老板看看向东山,再看看靳依林,“嘿嘿”讪笑一声,然后竖起大拇指,讨好道:“您二位一定是这个,半斤不晕,一斤不醉,酒量海着哩!”
“老板,你把我们俩吹大啦!不过说实话,就我们俩,吹个一斤七八两,问题还是不太大,你想,就这两个菜,够吗?”
向东山吐出一口烟雾,调侃地看着小老板。
听向东山这么一说,小老板顿时领悟,不好意思的笑着说道:“那是,那是,看二位大哥也不是抠唆之人。”
“好啦,好啦,要不这样,老板,再上两个你拿手的菜,四瓶啤酒当茶,不够再叫,好吗?”
靳依林不想再多啰嗦,手一摆打断他们,吩咐小老板道。
“好嘞!烧大肠一盘,烧腐竹一盘,再来四瓶青岛啤酒!”小老板响亮的吆喝一声,一个旋身去招呼别的客人了。
向东山旋开酒瓶盖子,将两人面前的牛眼杯斟满,霎时,酒的醇香弥漫在空气中,两个人举起酒杯,临水对月小酌起来。
向东山抿了一口酒,张开嘴巴哈出一口浓浓的辣意,而后放下杯子,盯着靳依林看了一阵,试探着问道:“这段时间你总是少言寡语,闷闷不乐,多云转阴,脸上咋就跟写了‘旧社会’三个字似的?”在他眼中,靳依林一直是个没有烦恼不知道忧愁的人。两人从中学到高中,从走出校门到去农村接受再教育,差不多有七、八年时间,几乎形影不离,无话不说,直到向东山从农村走入红色军营。
靳依林也觉察到自己沉闷的情绪和这里的气氛有点不协调,忙收回走神的目光,挥挥手,淡然一笑。“别球扯淡瞎猜,有酒有肉,有绿水,有清风,有明月,有蓝蓝的夜空,当此良辰美景,得写上‘共产主义’才对,哪来的‘旧社会’,真是胡诌诌!来来来,喝酒喝酒!”
靳依林岔开话题,故作轻松地举起酒杯。
向东山知他脾气,不愿说的话宁肯烂在肚里,沤成大粪,也不会吐露一字,当下也不再多问,微微一笑,举杯和靳依林一碰,扯过了话题。
此时,已是晚上八点来钟,只见一轮明月当空而缀,银色的辉光犹如一位纯情少女柔柔的目光,风情万种地俯视着南湖的水面,将她无尽的蜜意飘洒在地面上的万物,让人感到无比的惬意和舒爽。和风送温馨,夜景醉怡人。渐渐,市区的人们如倾巢而出的蚁群,挤满了碧水两岸,本是凉爽清新的秋风,逐渐被男人们散发出的汗臭味,女性身体氤氲出的香水味,烤羊肉串的孜然味及肉膻味所侵噬,空气逐渐混浊起来。 公子一朵花 我开百花杀 那些年,那些事,蹉跎岁月...... 第六章 妻子
玉兔东移,星辰稀疏。湖边玩耍的游人渐渐稀少起来。
靳依林向东山一瓶白酒已是底朝天撂在了桌下,两人又开始灌起了啤酒,正值酒酣耳热之极,向东山的手机骤然响起,他掏出一看,递给靳依林,“弟……弟妹打来的。”
靳依林怔了一下,这才醒悟,自己的手机是装在外衣口袋中,而为了替小玲御寒,外衣已裹在了小玲身上。
糟糕!麻烦来了!靳依林心道。
靳依林的表情顿时变得很窘,目光变得黯然起来。他蹙着眉头接过手机。果然,手机那边传来妻子怒冲冲的咒骂声:“死哪儿去啦!又灌马尿了还是去找小姐了!啊!干见不得人的事儿,手机也不敢接了?嫌我老了咋地!明天周末,要变天了,赶早去给你女儿送衣服!”容不得靳依林有插嘴的空儿,一阵连珠炮似的责骂声后,电话那边咔的挂了。靳依林心中一阵烦躁,热热的火气直冲嗓门,他用力咽下一口唾液,低低的骂了句“妈的!”
向东山晃晃脑袋,他虽有点醉意,但大脑还比较清醒,方才手机中的对话他听得一清二楚,也知道靳依林夫妇是反贴的门神,对不上面,平时吵架的次数倒比说话多,具体因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问,毕竟是人家两口子之间的事儿。
“怪……怪我,好……好了,该走、走了,可别和和……和弟妹生气,回去别、别多说话,只管睡……睡觉……”
向东山自责起来。
靳依林家住的巷子很深,只有巷子口那根高高的木杆上挂着一盏路灯,像一位老人半眯着的眼睛,昏黄黯淡的光模模糊糊地照着巷子。
靳依林七折八转,一直将自行车骑到巷子深处,到了自家门前,这才偏身下车。他在这条巷子住了将近二十年,闭上眼骑车,脚蹬转几圈该拐弯,都熟稔在心。巷子的路面是用四、五尺长的青石条铺成的,年长日久,被出出进进的人们的脚底板擦磨的光滑发亮。
椐说这条巷子很有些年代,很久很久以前是这座小城的风花雪月场所,烟柳巷。达官贵人,南来北往远来经商的巨贾们,吃饱喝足之后便来到这里,寻花问柳,以解走南闯北孤寂之苦,或烧上一泡大烟,临走撂下一把的银子或一沓钞票。后来为了攀比,招揽更多的生意,老鸨们将旧房拆掉,弄来青条细砖,用糯米汁拌白灰,把个尺把厚的屋墙砌的笔直,一溜线白色的灰缝,分毫不差,屋顶是用一尺见方的砖砧子铺平,再苫上小窑烧出的青细瓦,走进屋中真的是冬暖夏凉,心清气爽。二楼则用深山运来的,三寸来厚的松木做地板,土腊打磨,油光发亮,一股股松木的香气沁人心脾,……
来往的人多了,便在青石板上留下了深深的足痕。如今,那些老房大多已不复存在,都被拆掉盖成了国经房,只在靳依林家对过还留下一座这样的两层小楼,鹤立鸡群般竖在那里。
靳依林看看自家窗子,灯光全无,寂然无声,知道妻子早已睡下,便摸出钥匙去开房门。
一阵高跟鞋撞击石板的声音,“咯噔咯噔”,在这寂静的巷子里显得是那样的清脆刺耳,空气中一股香水味越来越浓,直往靳依林鼻孔里钻,弄得他痒痒的,很不舒服,不知是因为有点受凉还是香水味的作用,他连打几个喷嚏。紧接着一条长长的黑影飘了过来,那黑影长发披肩,身材苗条阿娜,细细的腰肢一扭一扭向这边走来。
黑影来到靳依林身边停下,又往他跟前靠靠,一个姿色妩媚的脸庞几乎贴上靳依林后背,黑影将手中的鳄鱼皮包往肩头一甩,打了一个咯,“吆,是、是依林大哥啊,去、去喝酒了吧?用不用扶啊?”
不用回头,靳依林就知道是对面那座小楼住着的叫叶红的女人。风传这女人一到晚上就弄得花枝招展,像一支鲜嫩的玫瑰,几百元的法国香水身上一阵乱喷,搞得跟旧上海十里洋场的交际花似的,出了巷子口来到街头小手一挥,拦下一辆矫的,绝尘而去,直到夜半才归,一屁股睡到第二天中午,下午打上几圈麻将,家中养了一个小白脸,日子倒也过得滋滋润润,逍遥快活
靳依林对这女人十分反感,不愿和这女人多说,口中“恩”了声,冷冷的道:“谢谢,不用。”说完就要推车进屋。
叶红见靳依林不愿多说,也觉没趣,便开了自家房门,刚要进屋,又转过身,眼帘飞快的眨动几下。“噢,依林大哥,对、对了,今儿下午大姐点儿有点背,输了钱,你回去可别惹着大姐啊!嘿嘿!”说完,叶红窃笑两声。
靳依林轻轻“啐”了一口,“啪”地将房门锁上。
靳依林住的是三间平房,他和妻子一间,女儿住一间,另一间当做客厅兼厨房。
妻子似已睡熟,靳依林轻手轻脚,找来换洗衣服,用净水将身子擦拭一遍,将脏衣洗净,这才夹了被褥来到女儿房中。
靳依林躺在床上毫无睡意,来回翻了几下身后,干脆坐起靠在床头,仰面大睁着两眼看着黑黝黝的屋顶,脑海中突然就想起了李平,想起了那三年的知青生涯。 怎么发不上呢? 请加QQ:2904998 四十,
活
亦或
惑:L:lol
页:
1
[2]